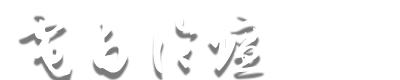历史惊人地相似,开门揖盗的巴勒斯坦人,即将成为另一个印第安人
迷途客
2025-8-17 12:28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1年11月的某天,在南达科他州的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门口,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正站在风里发抖。
他穿着不合身的白人校服,头发被剃光,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身后,几个同龄的孩子正被老师用英语训斥着。
没有人听得懂那话,可是没人敢不听话。
这不是孤例。
那时候,类似的场景在全美国的保留地边缘反复上演。
对这些孩子来说,离开家族、被迫改名、失去语言,不是选择,而是命令。
他们的父母多半无力反抗。
从1880年代开始,印第安人就被迫接受这样一套“文明方案”——说是教育,其实是抹除。
这一切的背景,其实要追溯得更早。
1620年,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殖民者生活艰难。
当地的瓦姆帕诺亚格人送来玉米、火鸡,还教他们挖蛤蜊、种南瓜。
第二年秋天,双方一起吃了顿饭,这顿饭后来被叫做感恩节。
可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情况彻底变了。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土地成了麻烦。
有些殖民者开始用契约、酒精、甚至武力换地。
到1675年,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爆发了所谓的“国王菲利普战争”。
那场仗打了一年,印第安人死伤惨重。
有人被贩卖到加勒比当奴隶,有人逃进深山,再也没回来。
这只是开头。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成立。
按理说,国家建立了,原住民也该被纳入保护范围。
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1803年,美国买下路易斯安那。
土地多了,眼光自然也放得更远。
那会儿西部还没开发,印第安人却早就住在那儿。
于是,政府开始制定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通过。
强制迁徙开始了。
最典型的是1838年的“泪水之路”。
乔治亚州的切罗基人被赶往奥克拉荷马。4000多人死在路上。
有人冻死,有人病死。
活着的人,到了新地方连水源都找不到。
后来到了19世纪末,事态变得更严峻。
1887年,《道斯法案》出台。
按法律,印第安部落的土地要重新划分,变成私人所有。
每个家庭分到的地不多,剩下的全卖给白人定居者。
账面上说是“教育基金”,可实际上大多数印第安人连自己的土地都保不住。
那年冬天,一位叫雷德·克劳的印第安长老在部落会议上说:“他们不是要我们的地,他们是要我们的影子。”没人敢接话,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意思。
与此同时,政府还推行了寄宿学校制度。
孩子被带离家庭,强制入学。
不能说母语,不能穿传统服饰。
有些孩子几年都回不了家。
学校里的待遇非常差,很多孩子营养不良、生病,甚至死在途中。
最严重的时期,一个寄宿学校的死亡率能达到30%。
1900年以前,美国已经建立了150多所这样的学校。
很多由教会运营,也有的是军队背景。
最出名的一所,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
它的创办者普拉特上校说过一句话:“杀掉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
语言听着冷血,但那时候不少白人就是这么想的。
对比来看,那会儿的中国正值清末,义和团运动刚被镇压,八国联军踏进北京。
国门外松内紧,朝廷焦头烂额。
可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没把少数民族的文化彻底消灭掉。
而在美国,印第安文化正在有计划地被一点点磨平。
1900年后,印第安人口几乎跌到了历史最低点。1870年还有30多万人,到1920年只剩不到25万。
更讽刺的是,这期间美国却以“民主灯塔”自居,把《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挂在嘴边。
说起来,那份宣言里也提到了印第安人。
可那段话说他们是“无情的野蛮人”,说他们“残忍地杀害边境居民”。
这话写在建国文件里,流传了两百多年。
到了20世纪初,印第安人终於被允许申请美国国籍。
但条件很苛刻:必须放弃部落身份,接受美国式生活,甚至要改变信仰。
很多人不愿意,结果成了“无国籍”的人。
既不是部落成员,也不是美国公民。
而就在这种背景下,另一边的故事也在发生。
1917年,英国外相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写了一封信,说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建“民族之家”。
这封信后来成了以色列建国的基础文件之一。
但那会儿,巴勒斯坦早就不是一片空地。
大约有75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儿。
他们种地、做买卖、过日子,跟这片土地有着几百年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剧变。
欧洲的犹太人刚刚经历了纳粹的屠杀,几百万人死于集中营。
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支持他们复国。1947年,联合国提出分治方案。
犹太人分到55%的土地,阿拉伯人不满,战争随即爆发。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
第二天,第一场中东战争爆发。
结果是,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
他们的家园被摧毁,祖坟被铲平,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注意到两个群体的相似处:印第安人和巴勒斯坦人。
一个在北美,一个在中东。
一个面对的是白人殖民者,一个面对的是建国后的以色列。
但他们的境遇,却有很多相通之处。
土地的失去、身份的边缘、文化的压制、难民的流离。
这些词,在两个地方反复出现。
1973年,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中问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你还记得你家在哪里吗?”那人回答:“记得,是在雅法市东边,有一口枣树井。
井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但那口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那口井了。
参考资料:
Dee Brown,《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Holt, Rinehart & Winston,1970。
Ward Churchill,《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City Lights Books,2004。
Benny Morris,《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John Toland,《Adolf Hitler》,Doubleday & Company,1976。
U.S. Congress,《Dawes Act (General Allotment Act)》,1887。
U.S. National Archives,《Indian Boarding Schools Records》,Record Group 75。